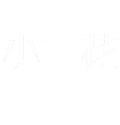“中国茶”申遗成功!见证茶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茶”申遗成功!见证茶文化源远流长
一盏茶里见乾坤
近日,我国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茶叶和茶文化的发源地来说,这个世界性的认证有点姗姗来迟,却也实至名归。
茶在国人的文化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节庆和仪式活动中饮茶、敬茶等习俗不可或缺,同时茶被赋予了浓郁的宗教色彩,比如流行的茶禅一味、在茶中明心见性等说法。同样是喝茶,当我们冲饮西式茶包之时,几乎无人会有这种想法。在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中,宗教色彩从何而来?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译著《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值得一读。作者贝剑铭是研究中国宗教史的汉学名家,他从日常习见的茶入手,结合传统中国宗教与文化变迁,列举了茶带有神话性质的起源、唐代以前的文献记载、唐宋直到明清的饮茶习俗的变更,分析了茶对传统习惯、审美、仪式、科学和知识观念方面的变化。译者是中国茶叶博物馆文博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朱慧颖,还参加了这次“中国茶”申遗工作。

偶然与必然
论及茶文化,陆羽及其著作《茶经》是绕不开的存在,而《茶经》也代表着中国茶文化经过几千年或明或暗的发展,终于有了一次系统的整理。茶文化史上最为精彩的也就是陆羽生活的唐代,贝剑铭在书中也花去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述那个时代的风华。
《茶经》出现于中唐时期,绝非偶然,但其出于陆羽之手,又充满了历史的巧合。
陆羽的身世也成谜,他从小被僧人抚养成人,却不想出家为僧,后来逃离寺院,卖艺为生。开元盛世给了他足够的机会,14岁的时候,被竟陵太守李齐物赏识,得以跻身文坛。安史之乱后,陆羽南渡,在南方广为游历,结交了皎然和尚、张志和、李冶、颜真卿等一大批儒释道背景的朋友。同时,陆羽对茶的研究也在日臻化境。
此时遭受重创的唐帝国,经济重心加速转移到了江淮地区,南方产的茶叶迅速成为行销全国的商品,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写到的“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日浮梁买茶去”——江西浮梁即是全国的茶业交易中心之一。唐代曾在780年开始征收茶税,后废弃,793年复征。可见,茶业在中唐以后在帝国经济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贸易的发展,催生出了文化的需求。古代中国,凡事都喜欢有据可查,讲究语出有典。尤其是做生意的,更喜欢把自己包装成文化商人。茶业兴盛,却未在文化上解决起源、名称、制作工艺等诸多问题,这让茶文化在源头上充满了不确定性。
茶虽然在唐以前漫长的历史里就已经参与到先民的饮食中了,但大都是南方局部地区的地方性食品,大部分做法并非做成饮品,如晚唐杨晔所撰之《膳夫经手录》记载,“今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直到6世纪,茶的做法仍然多种多样,作为饮品,还不是当时社会的共识。此外,茶的名字也并未固定下来,“槚、蔎、茗、荈、荼”,叫法五花八门,给相关的考据制造了门槛。还有起源问题,郭璞在《尔雅注》中提出四川地区是中国最早食用茶叶的地方,谁是第一位饮茶之人?
这些问题不说清楚,在门阀士族当权大为讲究出身论的唐代,茶的文化合法性就得不到确认——“因为在封建中国很难将一种没有文化渊源的新品推出,因此茶必须是古已有之。”所以,才有茶商找到陆羽,《茶经》也确实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商业化写作的专业书籍。陆羽的技艺、文化修为和朋友圈,也预示着他是这本书的不二人选。这就是历史的必然和巧合。
虽然是命题作文,陆羽的写作也并不容易,他761年完成初稿以后,便开始广为游历,一边对茶叶进行实地调查,一边修改《茶经》,直到780年,《茶经》才付梓出版,短短七千余字,凝聚着他20年的心血。
陆羽的“发明”
某种意义上来说,茶文化是陆羽为代表的唐代士人群体的发明。有了《茶经》,茶的价值才成为社会共识。
茶在陆羽笔下寻找到了“自我”。有了《茶经》的广泛传播,以“茶”来称呼这种植物,成了中唐以后的社会共识,明末学者顾炎武在泰山碑铭上的发现也佐证了这一点:“愚游泰山岱岳唐碑题名,见大历十四年(779)‘荼药’字,贞元十四年(798)刻‘荼宴’字,皆作‘荼’……其时字体未变。至会昌元年(841)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855)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
在处理茶的起源问题上,陆羽并未过多纠缠历史问题,因势利导,将茶的发现人定为神农氏。笔者转引贝剑铭的论述如下:“陆羽把茶的起源上溯至远古,实际上为后世固定了关于茶的官方说法。因此我们看到,饮茶本质上虽是唐代的发明,但它在作为新生饮品传播的同时又被赋予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和神话。茶承载着如此庄严的神话出现,这一点告诉我们:为茶提供这样一个非同凡响的背景故事反映了人们认为茶在当时的意义多么重大。”这是一种非常具备中国传统特色的操作,将茶视作神的馈赠,既能增加神秘色彩,又能抬高身家。
而陆羽的出身和交游也奠定了茶文化的宗教气质。陆羽在佛门长大,却追求入世,然后结交了一大批出家人做朋友,死后他又与僧人皎然的坟墓比邻而居。这种贯穿终身的身份悖离,并未给其造成困扰,反而让其对茶重新定位,除去了茶在饮食中的配菜功能,拔高了文化意义,且身体力行地赋予了茶文化宗教气质。
在陆羽的朋友圈中,不乏出家人与遁世的隐士,擅长写诗、制茶的诗僧皎然即是代表,皎然曾写过“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这首《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将饮茶的陆羽和饮酒的陶潜放在了等高的位置,也就等于向社会宣示了茶文化的超凡脱俗。

禅为茶助兴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进入万马齐喑的时代,求取功名难度加大,也不再是文人们唯一的选择,所以贝剑铭说“我怀疑755年的安禄山造反造成了嗜酒诗人作为文人榜样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红尘之外爱茶禅师的正面形象的崛起。”
佛教自汉代从西方传入中原,在唐有了长足的发展,佛门提倡酒戒,为茶的流行创造了客观条件。禅宗在中唐的兴盛,则让茶文化有了纵横天下的凭借,贝剑铭由此推断,“不管有意无意,禅宗的兴起与茗饮的发展在唐代文献资料中常常连在一起。”
在惠能及其弟子神会手里,佛教彻底完成了中国化,根据葛兆光先生的研究,在惠能的禅宗理论中,不再强调苦修,不用费尽心力地到达彼岸,“佛性常清静,何处惹尘埃”的观念使人们有了一种新的解脱方式,这种解脱方式就是不必解脱,回头看去,原来此岸就是彼岸,可以不用那样苦修也可成佛了,这个时候才叫大彻大悟。这个变化很重要,从后来禅宗发展的结果来看,惠能的这个思路使中国禅宗有了自我拯救的新方式,同时也使得佛教不再像是宗教,而只是一种精神信仰。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
饮茶,让禅宗的理论可以落地,一盏茶的时间,足够“顿悟”一个道理,饮茶的流程,也充满了禅宗的机锋意味。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开篇即说“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卢仝的《七碗茶诗》说得更为直接,“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茶在中国》认为,“唐代的茶事著述认为,茶能为作诗和坐禅提供必要的灵感和能量。因为茶的崛起和以诗歌及坐禅为特点的禅宗的兴起同时,二者最终在文化想象中相互交织,饮茶后来几乎被看作禅宗的同义词。”
茶与禅的世俗化
唐以后,没有了陆羽对茶文化创世纪一般的精彩。茶文化仿佛一座园林,陆羽给它设计了图纸并且初步建了起来,后世的人就是不断地进行精装修,让其愈加富丽堂皇。
宋代文化风气活跃,最为直观的是禅宗催生的新儒学的兴起,由此文人群体与出家人群体的进一步交融,如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中,苏轼等一干文人都身着宽大的道袍,苏轼也曾写过“吾心安处是故乡”充满禅宗思辨意味的诗句。宋代士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饮茶生活,起源于唐的茶百戏,在宋发扬光大,这种类似咖啡拉花的技艺,为饮茶增添了很大的观赏性和可塑性。斗茶的兴起,又为饮茶增加了趣味性。
同时,寺院在茶文化中的功能进一步增加。宋代的一些禅师因善于点茶而名噪一时,佛门的茗茶也不同一般,《水浒传》中鲁智深初上五台山,智真长老招待的茶即是,“玉蕊金芽真绝品,僧家制造甚工夫。兔毫盏内香云白,蟹眼汤中细浪铺。”同期,寺院中也首创了茶礼,满足世俗社会在宗教场所的需求。
历史行进到明清时期,茶文化更显了几分寡淡,贝剑铭却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晚明时期开始,僧人在文人的饮茶生活中,逐渐成为背景。好茶需要名水来配,寺院多在有茶有水的地方,明人认为水品中以山泉最佳,所以会为了一碗茶不辞辛苦遍访名山大川。袁宏道的《龙井》全篇只有一句“入僧房,爽垲可栖”提到了僧。贝剑铭认为“茶自身是讨论的主题:像许多时候那样,文人们在如画的风景中评水鉴茶,僧人只是这一严肃事务的背景之一”。
由此可见,茶与宗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毛细血管中,这些都层垒地融合在一起,走到今天,影响着我们喝下的每一口茶水。
中国茶,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滋养了几千年的历史,东渡日本促成了日本茶道的产生,且在近代,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轮船,走遍了全世界,时时振奋着几十亿人的精神。“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将会让更多人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明白一盏茶里自有乾坤。(何书)
【责任编辑:黄菲】